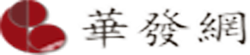香港高校應以高等教育國際化為目標
- 更新時間:2016-07-05 09:11來源:網絡作者:@aiman人氣:28069

2006年夏,時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黃子平出版了隨筆集《害怕寫作》,他反思“謙遜、謹言、慎思”這些這個時代稀缺的美德反倒讓我好奇,所以該書甫一出版時我就去信聯絡專訪,但是,他“害怕”了,婉拒了。緣慳一面這些年,當年策劃出版《害怕寫作》的朋友去讀博並留校任教了,我仍斷斷續續留心著黃子平的蹤跡:2010年從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休後,他曾回母校客座兩年;隨後,又轉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客座三年,以“沈從文八講”圓滿收官。
我關注作為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的黃子平,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當然還是因為他與錢理群、陳平原這“燕園三劍客”在1985年進行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也簡稱“三人談”)事件——
“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橫空出世,倡導以整體的眼光將中國現當代文學溯源至晚清,將“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三個時段打通,幾乎與滬上學者陳思和1985年提出“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同期,也成為陳思和、王曉明1988年正式實踐“重寫文學史”的先聲——洪子誠教授在他那部流傳甚廣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曾這樣評述“新文學整體觀”“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南一北兩大新穎命題的轉折意義,“1980年代中後期,這一文學曆史‘重寫’活動,得到了具有文學史形態的理論表述而凝聚和加強。”“燕園三劍客”中,黃子平或許是最具理論偏好的,然而他的慎思謹言中又藏著詼諧幽默。
30餘年來,黃子平的著述其實只有《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文學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學》等幾部,編選過一些香港的“小說年選”,但他在代表作《革命曆史小說》中首創了“革命曆史小說”概念,該書中有關“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成果也廣為學界接受。洪子誠在《我的閱讀史》一書中有專門的一章《“邊緣”閱讀和寫作》來談黃子平的洞見與性情——比如,黃子平對於現代小說中“病”的隱喻的精彩分析,對於“革命曆史小說”中的時間觀,以及對其中隱含的具有“顛覆”功能的“宗教修辭”的揭示,都不乏犀利之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黃子平有“第一小提琴手”的美譽,其獨到提法如“深刻的片面”、“創新的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功夫也沒有”等,也曾廣為學界稱道,但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是他個人學術寫作中自認為“最重要的”。然而,當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戛然而止,在1990年,黃子平突然遠離“中國文學”的“主場”,他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芝加哥社會心理研究所等海外學術機構訪學,直到1993年,在“回歸”前夕,才在香港結束這一段“漂泊”的旅程並開始長達17年的香江執教生涯。不解內情的人總喜歡追問,才華橫溢的黃子平當年為什么要離開聲譽鵲起的北大離開中國大陸。

黃子平“害怕寫作”,“害怕”過多地解釋自己,最近幾年,偶爾在滬上書評重鎮讀到過兩篇他的長篇訪談,似乎都是筆談而成,我仍心有不甘。當獲悉他將在2015年第26屆香港書展上與北大中文系“77級”同班同學、旅美作家査建英對談“跨語境、跨地域寫作的優勢與陷阱”時,我抱著響應“交談”的謙敬,終於約上了他的專訪——如果不是陳平原教授的高足季劍青博士提醒,我險些忘記2015年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發表30周年;1986年7月2日和10月25日,北大中文系曾就“20世紀中國文學”組織過兩次座談,後一次有日本著名學者竹內實、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參加,還有時任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語文系教授的李歐梵參加——今年,2016年,恰是這兩場座談舉行30周年。30年過去,昔日“燕園三劍客”中,1949年出生的黃子平——他長陳平原5歲,小錢理群整整10歲——也已退休五年多,在內地與台灣高校偶爾客座講學。
在去年的香港書展上,當我告訴“年度作家”李歐梵先生我將采訪黃子平時,他贊譽這位晚輩為“香港文學批評第一人”,還憶起錢理群、陳平原的導師王瑤先生在1986年10月那場中日學者對談中的精彩點評。最終,我在港鐵“炮台山”站附近一家咖啡館見到了黃子平,熙熙攘攘的市聲逼迫我們就近轉移到一家酒店的大堂,超過兩個半小時的交談涉及文學批評生態的變遷、香港的中學和大學教育現狀等諸多議題。這個變換場地的小插曲,或許也能表征人文社會科學在香港的命運,雖然香港高校的名教授們的薪水在亞洲乃至全球都令人稱羨,但黃子平和他的同道們恐怕本質上還處在這個喧囂工商社會的邊緣,他的一部舊著就取名《邊緣閱讀》,他曾自述:“‘邊緣’並不是與中心僵硬對立的固定位置”、“‘邊緣’只不過是表明一種移動的閱讀策略,一種讀縫隙、讀字裏行間的閱讀習慣,一種文本與意義的遊擊運動。”

當我斷斷續續修訂好這則長篇訪問記時,黃子平已結束新近在台灣“中央大學”的客座講學,2016年的新一屆香港書展已然臨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下半年即將出版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徐志偉教授主編的六卷本《中國現當代文學前沿問題研究讀本》,黃子平的兩篇長文《革命曆史小說》與《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即收入其中一冊《1950—1970年代文學研究讀本》。在專訪定稿的這段時間裏,偶爾在微信朋友圈裏還讀到黃子平轉發的那些屬於他閱讀強項的理論文章,偶爾收到他的郵件,他告訴我“香港連日苦雨”,6月3日午後的來信裏他還謙稱這篇專訪“談的都是些雞毛蒜皮,意思不大”,“連日苦雨”、“意思不大”這些淡淡的語詞,總讓我不禁想起素未謀面的忘年交、同樣淡泊名利的台大中文系榮休教授周志文先生。
就在6月7日,香港浸會大學官網公布了第6屆“紅樓夢獎暨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的六人入圍名單,最終結果將於7月中旬正式公布,黃子平是這一獎項的決審委員,其出資人、香港彙奇化學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大朋是黃子平“唯一一個沒有畢業的碩士研究生”,這位經曆傳奇的商人一度給出了當時華文文學獎裏最高的單筆獎金。“曆屆獲獎的有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駱以軍的《西夏旅館》、王安憶的《天香》和黃碧雲的《烈佬傳》。”盡管評審任務繁重,但黃子平對未來充滿信心,“照這樣辦到第十屆的話,這個獎就站得住了。”
燕舞:關於“燕園三劍客”30餘年前互相切磋問學的情形,在你們三人合著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一書中,其實,陳平原教授對與您的相識、互動多有回顧,那么,您和老錢(理群)最早是怎么開始交往的?
黃子平:我那時候的女朋友、現在的太太張玫珊是從阿根廷回國的僑生,來北大讀中文系,當時外交部很關心她,說北大本科的獎學金太少,不夠花,讓她按照研究生的待遇來讀,可能會多幾塊錢獎學金,於是她就變成王瑤先生門下那一群大哥哥、大姐姐的小妹妹,跟在他們後面求學。我是經過她又認識了他們。那時候錢理群、吳福輝和鍾元凱在研究生宿舍住一個屋,我經常跑去跟他們聊天。
1984年碩士畢業以後,謝冕老師讓我留在中文系教書,當時的系主任嚴家炎老師也堅持要我留在系裏,結果系裏說不能留。孫、謝兩位老師沒辦法,就去找北大出版社社長麻子英,他整天披著一個軍大衣,非常豪爽。他們出版社當時大概也沒有什么有碩士學曆的員工。後來我才知道,這兩位老師覺得系裏的黨委書記過兩年就退休了,他們讓我在他退休後再回到系裏。
在北大出版社文史室當了快兩年的編輯,1986年才回到系裏,教書大概教了不到四年,1990年就離開了。在北大出版社那段時間還是比較空閑,後來發現我學東西最多或者說跟老錢、平原他們在一起交談最多的時期,正好就是1984年、1985年、1986年。當時出版社來稿很多,但能用的很少,大量時間都用來做校對,那時候出版社出《三國演義》彙校彙評本,經常背著校稿跑到國子監去看《三國演義》的孤本,這些工作都是些技術性的活兒,到了晚上就可以寫東西了。
那時候,北大中文系裏孫老師、謝老師他們對年輕人是特別愛護的,考慮很周全,他們再上一代的老先生們,比如林庚、王瑤、吳組緗的年紀都很大了,只上一點選修課,我們文學“77級”、“78級”算是最後一屆能修老先生們課的本科生。當時每次去聽他們的課,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機會。
非常諷刺的是,恰恰是北大和複旦這兩所分別提出要“打通20世紀中國文學”、要“重寫文學史”的這一南一北兩所名校,只有他們才有現代文學史教研室和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區別,別的大學這兩個教研室都合並起來了。這兩所大學都是最早設當代文學碩士點的,當這些碩士生留校以後,他們的師資力量比較強了,所以要想把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兩個教研室合並在一起並不容易,於是發明了很多“理論”來論證分開的必要性。
燕舞:多年以後,文學史家們將您和老錢、陳平原合稱為“燕園三劍客”。當年,應該是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先發表,然後才是《讀書》雜志組織你們進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
黃子平:“燕園三劍客”是傳說化了。對,後來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得以促成也很偶然,有一次我跟平原一起去《讀書》雜志社,聊的好像是他們要開的一個關於“批評的批評”的專欄。我突然靈機一動,說我們仨有這么一篇論文,有一些前期共同討論時的錄音材料可以整理出來,此前沒有想到那些錄音會有用。那么大一個選題,月刊一年才十二期,“三人談”連載六期,當場就拍板了,那時候《讀書》編輯部主事的是董秀玉先生,非常有魄力,吳彬女士那天也在。

後來我們發現,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這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文學評論》先期刊發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反而沒有那么大。先在《文學評論》上刊發,老錢跟編輯王信、王行之他們熟。老錢總是很興奮,文章還在討論醞釀,他就到處跟朋友們說有什么設想,王信他們馬上就說“這篇文章一定要給我們”,這就是1980年代的作者和編輯之間的關系,這種情形是後來比較少出現的。
比如說,我1983年在《文學評論》最早發表的那篇評論《“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林斤瀾近年小說初探》,其實文章雛形是我在北京作協一個很小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我們的導師謝冕先生是北京作協理論部的成員之一,當時理論部要開一個關於北京作家的小型研討會,導師就給我們派了任務,一人挑一個述評對象,我就挑了林斤瀾,季紅真挑的是汪曾祺,張志忠挑的是鄧友梅。我挑了林斤瀾以後,才發現林斤瀾是如此的不好讀,如此澀、怪,下了很大功夫去把能找到的林斤瀾早期作品和後來寫的作品都找來。一開始只是座談會上比較詳細的發言,還沒有成為獨立文章,《文學評論》的編輯楊世偉老師在座談會下,馬上就說“你把它寫出來給我”,於是我就吭哧吭哧地寫出來。寫出來之後,楊老師只給我刪掉了兩個四字短語,這次修改讓我一輩子受用——第一個是“毫無疑問”,我那時候很喜歡用這個短語,楊老師說現在沒有什么是“毫無疑問”的;第二個短語就是“眾所周知”,他說都已經是“眾所周知”了,你還說它幹什么?我馬上領悟到,第一,不要說死話;第二,不要說廢話。這篇論文刊發後,還拿了中國社科院理論獎的三等獎。後來,楊老師請我到他家吃飯,我第一次看到老北京人家裏面做涮羊肉的全部程序,調那個醬時腐乳跟芝麻醬是主要的,然後怎么切那個羊肉片,很有意思。一個老編輯把年輕的作者當朋友,現在很難想象了。我和許子東還到過王信非常簡陋的家裏,呼嚕呼嚕吃西紅柿雞蛋打鹵面。我後來在學術會議上經常看見一群大學教授圍著什么“核心期刊”的小編輯團團轉,心想,今夕何夕!
後來讀到《王蒙自傳》,他還提到我這篇文章,說他見了林斤瀾,跟林斤瀾說他讀了這篇評論感動得落眼淚,林斤瀾冷冷地回了一句,說“你還有眼淚?”接著,王蒙一通發揮說是“淚盡則喜”。
1980年代的老編輯很會抓選題,他們主要做兩件事情,一是選到對的作者對的題目,二是選到了就催促他們盡快去寫。當時,《讀書》雜志每個月月底有一個“讀書日”,就是一幫學者喝茶聊天,編輯們穿梭其間,經常突然間抓住一個題目,就讓某位學者給他們寫。1980年代,圍繞這些刊物的作者圈的,也是一種“交談”,這是很重要的,畢竟文學刊物的生產機制只看刊發後的文本是看不出全貌來的,就是要交流,要“交談”。其實,大學也一樣,像美國大學裏很重要的一項活動就是他們的brownbaglunch,就是中午時分不同系的教授在一起吃簡單的午餐,他們每人拿一個褐色紙袋在那兒聊天,經常會聊出很有意思的課題,你這個學科的研究題目會啟發另外一個學科的學者。
在大學裏面,這種“交談”是最重要的。我1998年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所訪問過一段時間,日本的大學是另外一種研討方式,他們一般有一個常年堅持的讀書會,像他們的“30年代中國文學讀書會”,幾十年來就讀那本《現代》雜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一句一句地讀,幾代學者就這樣讀下來。我參加過這種讀書會,他們一個很好的規矩,就是讀完以後就去居酒屋喝酒,教授掏錢,學生不用掏錢。一些在日本訪學過的學者回國後,想在北京照搬這套讀書會的做法,發現不知道為什么行不通。
燕舞:您1990年離開北大遠赴海外,是因為您夫人是僑生的關系,還是有其他更為複雜的原因?我看到後來留校的吳曉東教授回憶,您當年的課特別受歡迎;陳平原教授也特別懷念你們“燕園三劍客”當年融洽的討論氛圍。
黃子平:有大時代的原因,但也不完全是,正好那段時間要去阿根廷探親,探親之後到了美國,正好李歐梵先生在芝加哥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有一個研究計劃,他申請到一筆“盧斯基金會”的研究經費,計劃研究後“文革”時代的中國文化,盧斯(李歐梵喜歡譯成“魯思”)是傳教士的後代、《時代》雜志的老板,他對跟中國有關的研究項目很肯給錢。歐梵一看我經過美國,說“正好我們要請你來”,所以我就留下了,當時跟北大中文系請了幾個月假,一共待了一年多,後來要續假時北大不同意,就算我滯留不歸了。這個項目的參與者還有許子東、李陀、劉再複等人,那時我們湊在一起,天天討論,正好那時候“現代性”的問題開始討論得比較多。這個項目結項的時候開了一個研討會,參與者各自提交了一篇論文。我當時提交了一篇關於丁玲小說《在醫院中》的討論,可以明顯看到裏面有討論到“現代性”的問題。後來,歐梵調到洛杉磯大學去了,我就到了伊利諾伊州大學香檳分校,待了一年多,開始做“革命曆史小說”的研究。東亞圖書館才不管你這些書在冷戰方面如何“漢賊不兩立”,它們就這樣親兄弟一樣肩並肩地站在同一排書架上,我非常震撼。這種震撼是不同的分類學帶來的震撼。所有的教育或者說學問,最基礎的部分都在分類學。其實,從小學開始,老師就開始教我們怎么分類,此後接受的教育是越來越複雜的分類。所以,有時候所謂知識或者研究范式的轉換,只是不同的分類學出現了,原來不是一類的知識突然被合並成一類了,或者原來屬於一類的知識變成了兩類。
我很幸運,在1990年離開北京之前,正好有一個台灣文化人郭楓,他有一筆錢,又是一個“統派”,跑到大陸來組織了一批書稿,台灣一家出版社要出,後來他的生意又不行了,這些書稿就擱置在台灣。我在芝加哥大學時參加哈佛大學召開的一次“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年會,認識了包括王德威在內的很多後來的老朋友,就跟他提起擱置在台灣的這部書稿。他當時正好跟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有合作,書稿就很順利地轉到那裏出了,就是《幸存者的文學》那本書。1993年從伊利諾伊州大學香檳分校回香港,是因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正好有一個教職,當時是陳國球教授當系主任,他就是拿著這本論文集跑到他們文學院院長那裏,往那個英國學者辦公桌上一擺,說“我們要請這個人”,居然就通過了,我居然不用面試,也不用飛過來試講。等我1993年到了浸會大學中文系時,陳國球教授已經調到剛創立兩年的香港科技大學了,接替他的系主任陳永明教授安慰我說,“我也是剛來的”,但他可能有點擔心我的大陸背景,就去問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好朋友小思老師,“這個人到底怎么樣”,小思老師很鄭重地說“這個人如果你不請,我們都要請了”,他一下子就放心了。我很幸運,一輩子不管到哪兒去都沒有被面試過。
到了浸會大學中文系,必須“古今中外”的課程都教,不能只教當代文學專業,除了語言學方面的課程沒有開過,我光講“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就講了十幾年。當初在北大讀本科時,“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門課我曠課最多,因為當時我對“性靈”說、“神韻”說這些都不感興趣,但通常越是曠課的課考的分數反而越高。老天懲罰我,讓我教“古代文論”十幾年。在浸會教這門課時我就開始惡補,平原君就笑我說,讀了“性本善”就去教學生“人之初”。
燕舞:“南來文人”群體在香港學術社群的融入也是我很感興趣的議題,您的老家廣東梅州本來是講客家話,但當年下鄉海南時習得的粵語,顯然有助於您融入也講粵語的香港?
黃子平:對,當年在海南島國營農場下鄉插隊時,跟廣州來的知青在一起混,混的時間長了,日常的粵語就會了。其實,我剛來浸會的時候,學生們聽我的普通話比較困難——第一堂課上有一個選項,即征求學生們授課到底是用普通話還是粵語——結果,大家都舉手說用粵語。我說你們損失大了,因為我用粵語講課很不生動。後來,浸會開了一個“MA(一年授課型研究生)課程”,收了很多內地來的學生,跟MA上課時就改用普通話了。內地來香港求學的學生比例越來越高,這些學生學粵語也學得很快,尤其是女生,他們不少人都是語言天才。融入大學對我來說倒沒有問題,但要融入本地的文學“界”就需要一種自覺。我自己比較自覺,因為我是做文學評論的,所以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參加到當地的文學活動裏,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評獎等其他活動。所以,我跟本地的香港作家有很多交往,與那些本地年輕人辦的文學雜志都會有接觸。
參與文學類評獎也少不了,香港曾經幾乎所有文學獎都請我當評委,有些是沒有酬勞的,我也會答應。曾經有學生統計了一下曆年參加文學獎的評委人選分布情況,據說我排亞軍,冠軍是接觸了很多年輕人的詩人葉輝,文青們叫他“葉輝叔叔”。香港最主要的文學獎就是由藝術發展局主辦和資助的,由香港圖書館操辦。
有一個上海籍的老先生張大朋,他是1960年代的大學生,很聰明,高考考分很高,但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就被調劑到北京石油學院,當時正值“困難時期”,分配工作的時候分到了蘭州。他去蘭州實習過,知道那個地方是不能待的,否則可能要死掉,所以就沒有服從組織分配,回到了上海。這是當年非常特殊的現象,不服從組織分配的人竟然戶籍能退回到上海,可以作為一個無業人員在上海待著。
後來,他來了香港,做本行化學工業,成了“香港彙奇化學有限公司”董事長。1997年之前移民到了加拿大,突然發現肝硬化了,要換肝,手術很成功,他躺在醫院裏,不斷有人問他換肝手術的注意事項,他回答得很煩,幹脆就寫下來,寫完之後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寫文章,就寫了這么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這位老先生很有意思,後來他給自傳取了一個很適合在機場書店賣的書名,也可以說是一種“標題黨”。後來,老先生就跑到浸會文學院來要讀研究生,他年紀比我還大,鍾玲院長就建議他讀我的碩士研究生。我一看是上海人,就建議他寫一部小說來代替論文。讀到後來,他不感興趣了,他是我唯一一個沒有畢業的碩士研究生,爛尾了。但是,他打算弄一筆錢出來辦文學獎,決心給出當時華文文學獎裏面單筆獎金最高的,當然現在已經不是最高的了。當時,我建議他獎助長篇小說的創作,後來發現這個建議很糟糕,因為我們每年都要讀至少七八部長篇小說,有些長篇小說是上下兩卷或者上中下三卷甚至多卷,這個工作量很大。劉紹銘教授是第一屆評委會主席,第二屆他就退任了,太辛苦了。曆屆獲獎的有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駱以軍的《西夏旅館》、王安憶的《天香》和黃碧雲的《烈佬傳》。照這樣辦到第十屆的話,這個獎就站得住了。
燕舞:您的個人閱讀似乎流露出較強的理論偏好,甚至,就在今年5月11日,我還在您的微信朋友圈裏看到那篇哲學家阿甘本關於“警察在例外狀態下的主權治理”的論述——警察是暴力與主權之間構成性交換的赤裸地帶。也請您介紹下您在浸會大學曾堅持了長達十年的周末“理論經典讀書會”這一“少數人的讀書會”。
黃子平:我在香港參與的那個“理論經典讀書會”,一般幾乎每周六下午都有,有時是兩周一次。那時,一方面我帶的研究生不少,在香港,我們浸會大學的研究生名額本來是不多的,正好碰上帶研究生不計入教員的工作量,別人不願意帶我倒願意帶,官方統計證明我帶下來的研究生人數占整個文學院那么多年的總量的三分之一;後來帶研究生要算工作量了,我就不帶了,因為有爭奪資源的感覺。
“理論經典讀書會”差不多從新世紀初開始,持續了近十年,到我2010年退休為止。它也吸引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學校的一些碩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們,參與者十年間進進出出,要在香港這么忙的一個地方堅持讀書,我自己都很驚訝能夠讀那么久。
基本上,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家的著作我們都讀,李歐梵先生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博士生叫張曆君——博士畢業後留校在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擔任助理教授,他讀書很多,而且理論上非常敏感,所以當時我們所有的閱讀書目都是由他推薦,每一次會有一個人主持。通常,我負責緒論或第一章和最後一章,爭取能夠把它盡量地貫通起來,我自己也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每部理論專著都按章節分給每個參與者,分好每個星期誰講這一章,講完之後再進行問題討論。之所以分章節給每個人,是因為理論書往往都很難的,一個人讀很辛苦,如果有一群人讀,互相比較、問難,那就會好讀一點。
我們的周末理論閱讀以理論家們已出的中文版著作為主,讀不通的時候就選擇外文版本來翻,有時候會拿外文原著比對著讀,有些專著的翻譯很糟糕,像北京三聯出的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我們就讀出很多不通的地方,越是中文很順的地方越是有問題,這往往就是翻譯的問題。有一段時間我們對已故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德勒茲很感興趣,就讀了他,讀了很久,學生們參考德勒茲的“小數文學”理論來討論香港文學,有很多洞見。我退休前大家讀的最後一本是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的《例外狀態》。我們的閱讀過程中有討論,也有很多爭論,倒沒有分歧特別大的時候。這樣的閱讀有一個好處,就是參與者們不會純粹地讀理論本身,通常他們也有自己在研究的題目,所以會跟他關心的另外一個問題串聯起來,跟純粹讀理論還是不一樣。比如,理論著作中舉過的例子,參與者會用另外的例子來補充,或者提出反例。
有一年香港科技大學開會,劉劍梅她們定了“當代寫作和荒誕”的題目,邀請我去做一個發言,正好我們那時候在讀阿甘本,所以我引用了他的論述。之後,我聽中文大學的老師說,那年中大學生的論文裏到處都是阿甘本,這些作者就是參加那次研討會的學生們。理論的“旅行”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路徑。
香港的大學有一個好處是可以跨校修學分,比如我的學生可以去科技大學聽陳建華教授的課,或者到嶺南大學去修鄭樹森教授的課,所以課堂上往往會有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全港的大學圖書館也都是相通的,可以跨館借書。
燕舞:誠如子平教授所言,1980年代以來,香港的中學一批有經驗的教師的流失,帶來的後果非常嚴重,比如,它直接導致香港的大學生源質量的下降。而談及中學教育,我記得香港中文大學的榮休教授小思女士也曾做過中學老師,而且香港的知名作家和大學教授中不乏做過中學教師的。
黃子平:對,而且小思老師教過的學生,大多畢業後都是去當中學老師,她是特別關注中學的一個教授;內地,我的老朋友錢理群也特別關注中學語文教育。很多時候,他們可能都會有相通的感受,內地的教育也是危機重重。
燕舞:您也曾談到過高等教育的“麥當勞化”。
黃子平:“麥當勞化”就是你親眼目睹了教育怎么樣成為產業,不光目睹了,也經曆了,後來發現內地高校的擴招更厲害。我在浸會大學中文系被分配設計“MA(一年授課型研究生)課程”,其基本理念就是要招夠多少學生才能夠不虧本,所有的舉措都是圍繞這個理念來設計,我都崩潰了,我最不適合幹這個。
燕舞:前面也講到香港的流行歌曲和香港電影,這些一度很發達的流行文化門類,對做文化研究的學者來說可能正是一個難得的學術田野——香港本地年輕人的文學閱讀有限,能夠直接依賴於文本的文學教育就相對薄弱。對於您做文學批評和研究來說,這個城市有什么影響?
黃子平:我自己做的直接的文化研究很少,因為考慮到讀者,而且我沒有關於電影方面的訓練,看電影純粹是為了放松和欣賞。浸會大學中文系一直沒有開這種電影課,因為學校裏本身就有很強的傳播學院和電影學院,學生有需要的到那兩個學院修課就可以了,我在浸會大學反而沒有這方面的壓力。
大學生需要更廣闊的國際視野,這點相信很少人會有異議。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際進展如何呢?當前,英國只有6%的高中生出國留學(微博);在日本和台灣地區,出國念書和畢業後出國工作的人,過去10年也有所下降。香港地區的調查也顯示,83%的本地大學生不願畢業後到外地發展。
今天,我們的孩子會在假期隨家人外遊,也會與同學參加交流計劃,他們踏足過世界許多地方,但對於這些城市的文化、日常生活和問題,他們又知道多少?他們是否知道東京面臨核能存廢的兩難抉擇?是否清楚倫敦人對政治的不滿?是否了解舊金山居民對同性戀的看法?或者是否領略巴黎對勞工權益的擇善固執?他們又是否認識其它遊客鮮少踏足的城市和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如性別歧視、社會不公、濫用毒品、剝削兒童等等。我們在報章和電視所見到的圖片和影像,是否真的反映了世界的真實面貌?
國際化並非盲目學習和采用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而不問其是否更優勝;也不是玩弄國際師生人數的數字遊戲,以提高學校的排名;更不是獨尊英語為唯一的授課、學習和研究語言。
我們應該學會更透徹地了解全球議題和其它地區的問題,並讓其它地區明白和欣賞我們的文化。我們應明白文化的多元化和差異,同時保持自己的身份和特點。我們應該走向世界,基於如下三個原因:培養我們年輕一代的國際視野,讓他們成為明日的世界公民,畢業後能遊走各國,有更廣闊的天地;借研究和學術合作,協助世界處理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讓西方認識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加強我們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
根據澎湃新聞網、人民日報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 凡本網註明"来源:華發網繁體版的所有作品,版權均屬於華發網繁體版,轉載請必須註明來自華發網繁體版,https://china168.org。違反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 本網轉載並註明自其它來源的作品,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不承擔此類作品侵權行為的直接責任及連帶責任。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轉載時,必須保留本網註明的作品來源,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
- 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周內與本網聯系,否則視為放棄相關權利。
- 李家超:破壞力量仍然存在 絶不能掉以輕心
- 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 香港分會場氣氛熱烈
- 特區政府斥英國報告抹黑新選制
- 梵蒂岡任命香港主教!「反港獨」神父周守仁擔任,臺唯恐面臨斷交
- 深圳推《前海方案》44條 支持港高校建新研究機構
- 把握机遇/港借“双循环”打造法律服务平台
- 林鄭月娥:破壞國安不能接受 有信心警方妥當運用權力
- 融入“雙循環”的香港明天會更好
- 要求加拿大釋放被美國 迫害的中國公民孟晚舟
- 梁振英:激進化如毒癮禍害青年
- 1《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鄭宇碩收美國錢搞「佔中」鐵證陸續曝光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政治和法律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一切鼓吹國家分裂的主張和行為,衝擊「一國兩制」,背離「一國兩制」與基本法。鼓吹「港獨」的政客和團體,在香港沒有任何生存空間,[詳細]
- 2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

這是一本自述體的書籍。作者根據自己擔任占中組織者的助理期間,在日常工作中接觸到的大量真實資料,經過細心的整理而成。當占中組織者信誓旦旦地公開說謊誤導香港民衆,沒有外國勢力參與占中活動的時候,由作者披露出的事實卻是,外國勢力主導和支持了占中等[詳細]
- 3愛國愛港就要勇敢地亮出來——夏雲龍博士與香港民間團體交流會紀實

6月3日下午,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華發傳媒總裁夏雲龍博士一行3人,在香港觀塘巧明街迅達工業大廈8樓A座的保健海流協進會辦公室,參加香港民間團體負責人座談會。該座談會主題為“愛國愛港亮出來”,由保衛[詳細]
- 4田飛龍:港青國民意識現危機 須重啟國民教育

田飛龍“占中”的重要政治遺產就是香港青年世代走上政治舞臺,形成香港社運新生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既[詳細]
- 5美國「以港遏華」和「以華制華」的政治陰謀路人皆見

從中美貿易戰開始,我便估計香港難以置身事外,不能倖免,過去數月香港發生種種示威遊行,均有美國的手影存在,現今想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更是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務,並展示對亂港派的支持。 [詳細]
- 6從《何為證據》看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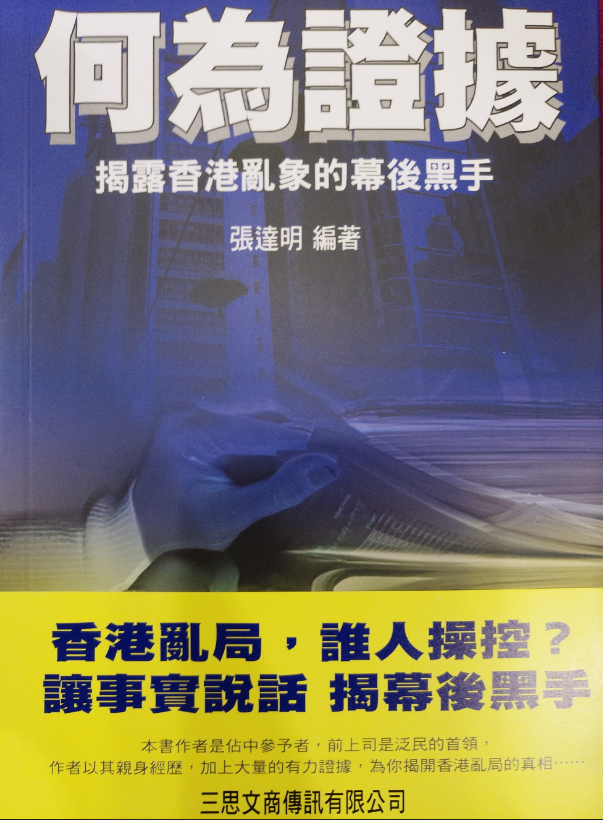
《何為證據》羅列了一系列極具震撼力的證據,「揭露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讓讀者有機會看清「佔中」背後的外國勢力身影。編著此書的張達明先生不顧視力受損,在過去七年鍥而不捨地蒐集和整理第一手資料,以鄭宇碩的言行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披露「佔中」背後[詳細]
- 7法庭對犯罪審判的輕判或拖延,都是對正義的否定

2016年3月31日下午2:30 - 4:30,由亞太法律協會主辦、香港公民協會合辦的【“佔領運動”以來的相關案件評析報告發佈會暨研討會】在香港中環中心專業聯合中心B報告廳舉行。報告會由香港公民協會林國華主席主持[詳細]
- 8“港獨”不除 國家安全堪憂

香港的 “港獨”分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不會輕易拋頭露面,他們躲在背后煽陰風、點鬼火,或是暗中提供資源等幫助,或是明火執仗為涉嫌違法犯罪分子狡辯;第二類是以學者身份、藉理論探討之名,向第三類 “港獨”分子灌輸 “港獨”思想,他們的歪理雖然[詳細]
- 9【香港書展2018】《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新書簽售賣爆現場

7月18日上午,香港作家張達明攜新作《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亮相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詳細]
- 10吳鵬飛:給港獨敲響一記警鐘,也給國家提個醒

港獨最近鬧得很凶,先是有人在英國註冊香港獨立黨,後來又有人在香港成立事實上以港獨、公投制憲為政綱的政黨,其發起人又是要參選立法會議員,又是應邀到美國大學演講,又是寫文章鼓吹。表面上好像很熱鬧,實際上是[詳細]
- 11嚴懲黃師黑暴 執政者快上訴

我們「保衛香港運動」代表全港市民,强烈不滿及堅決反對法官高浩文放生多次發表仇警言論的黃師譚玉芬,她企圖煽動羣眾攻擊傷害警員及其家屬,也令入世未深的學生和年青人觸犯暴動罪而前途盡毁。 社會大眾在2019年[詳細]
- 12嚴厲警告歐盟 停止詆毀香港

今日我們「保衛香港運動」來到歐盟駐港辦事處這裡,是要强烈譴責歐盟及七國集團抹黑香港國安法,誣衊23條生效後在香港生活、工作和經商變得更加困難。我們嚴厲警告歐盟及G7立即停止損害香港國際聲譽、立即停止干預屬[詳細]
- 和氣生財6/李家超:推廣禮貌服務 提升香港魅力
-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赴北京述職
- 吸引力足/寧德時代來港落戶 設國際總部及研發中心
- 免簽生效 到中國經商旅遊更方便
- 特區政府斥美打「法案牌」干預港事務
- 高鐵載客量超越疫前 短途增幅大
- 民進黨處心積慮搞「台獨教育」
- 市區「輕微僭建」 研申報後暫緩執法
- 情牽兩岸/創業台青深耕國漫IP 傳播中華文化
- 施政報告前瞻/設中醫藥專員 建數碼化中藥平台
- 兩岸京劇一脈傳 好戲連「台」見情深
- 投資信心提振 恒指連升六日共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