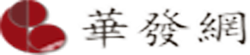史家陳垣廣惠學林
- 更新時間:2019-01-13 09:56來源:網絡作者:@Mary人氣:347764

圖:陳垣(見圖)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網絡圖片
去年六月我於本欄介紹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新亞研究所任教而經史兼擅的牟潤孫時,提及他的經學受自晚清國學大師柯劭忞,史學則師承陳垣,亦即時人及後學尊稱的援庵先生。原籍廣東新會的陳援庵與祖籍江西的陳寅恪,學術界合稱之為「史學二陳」。
陳垣(一八八○至一九七一)自幼熱衷國學,少年時代雖未中舉,但畢生篤行儒家「經世致用」的信念,一邊鑽研學問,冀以救國匡時,一邊教學啟育,扶掖後學。由於他學問精博、考究嚴正、誨人不倦、廣澤後進,深得各方推崇,後世景仰。
陳援庵雖然著作不少,但歷年可以買到的刊行本,並不算多。猶幸目前可在坊間買到的寥寥幾款,尚能代表他畢生學術上最精擅的幾面,計為:全面闡釋古代史籍忌諱的《史諱舉例》、專門治理校勘學的《校勘學釋例》、涉及民族史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及關乎史學史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
《史諱舉例》補前人不足
先談他寫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的《史諱舉例》。所謂避諱,是指但凡行文不得直書本朝前代或當代君主之名,以示崇敬,未敢冒犯,因此須以各種方法規避。查避諱之舉,初見於周,後成於秦,再後廣興於唐而盛極於宋。及至明清,避諱之舉,仍然流傳;民國之後始廢。
避諱之舉,固然有其美意,但對於後世研究前代,的確產生流弊,蓋因行文時須顧及忌諱而須予規避,結果造成混淆,徒添研究困難。不過,有些時候,壞事也可變成好事。學者可以運用忌諱知識,協助破解古籍裏的疑團,以及辨別古籍的真偽及真正的成書年代。這是因為忌諱的字,各朝不同,歷代各異。從另一角度看,諱字不失為每代的標記。因此,陳垣在《史諱舉例》序言指出:「研究避諱而能應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者,謂之避諱學,避諱學亦史學中一輔助科學也。」
既然避諱學有助史學研究,歷代史家學人,當必有所述及,例如周密《齊東野語》、洪邁《容齋隨筆》、顧炎武《日知錄》等筆記類的記錄,以及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陔餘叢考》、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史籍考證,均有所記述,當中以《廿二史考異》最為豐富。可惜,以上論著內有關避諱的載述散見諸章而毫不集中,而另外如周榘《廿二史諱略》、黃本驥《避諱錄》,雖然專論避諱,但謬誤頗多,不足為範。陳垣有見及此,銳意在避諱範疇著述新書,將前人所述,勘誤編整,以清晰明確的條目,一一呈示,方便縱覽。
《史諱舉例》全書有八萬餘字,共分八卷,依次是「避諱所用之方法」、「避諱之種類」、「避諱改史實」、「因避諱而生之訛異」、「避諱學應注意之事項」、「不講避諱學之貽誤」、「避諱學之利用」及「歷朝諱例」。
書內「卷一:避諱所用之方法」列明避諱之法有四,即「改字」、「空字」、「缺筆」、「改音」。四者之中,以「改字」最為普遍,即是將須予避忌的字,改成另一字。例如為避漢高祖劉邦的「邦」字,便將之前及當時的典籍內的「邦」字,一律改為「國」字。如此一來,《尚書》「安定厥邦」一詞,便須改為「安定厥國」。又例如《史記》為避諱惠帝劉盈的「盈」字、文帝劉恆的「恆」字,景帝劉啟的「啟」字,把恆山改稱常山、微子啟改作微子開、盈數改作滿數。
從上可見,但凡避諱改字,所選用之代替字,斷非貿然亂選,而須遵守「取共同義」的法則,務求方便後人追索。至於「空字」一例,是把犯忌的字從缺不寫,空出一格,而所缺的詞意,則須讀者自行猜度。不過,「空字」一例裏,還有三種「看似非空而實空」的做法,即是在須予留空的字位裏以「某」、「諱」或「上諱」之字填補,例如《史記》「孝文本紀」提及:「子某最長,請建以為太子」,當中的「某」字,是避劉啟即後來景帝的「啟」字。
至於「缺筆」一例,則較易處理,在書寫時只消將整個單字減去筆畫。這種減筆的做法,陳垣認為始見於唐朝。例如高宗乾封年間,「世」字改作「卅」字。這種「缺筆」的做法,與戲曲裏紅生勾臉扮關公時須在紅臉上添加一黑點,以示未敢冒犯關羽尊容,倒有些異曲同工,原理相同。無論是減筆而不把在上者的名諱以完整筆畫寫出,抑或在關公紅面上多加一黑點,都是心存崇敬,忒也有趣。
陳垣亦在卷未提及「避諱改音例」,而「避諱改音之說,亦始於唐。」不過,他在首段言明:「然所謂因避諱而改之音,在唐以前多非由諱改,在唐以後者,又多未實行,不過徒有其說而已。」換言之,改音之例,只有理論而無實例。陳垣在首段之後隨即提出大家耳熟能詳的「正」字讀「征」作為例子。故老相傳,「正」字讀作「征」,例如正月讀作「征」月,是為了避始皇正的「正」字而改讀「征」。然而,據陳垣所指,《詩經》「齊風」內「終日射侯,不出正兮」的「正」字,須讀「征」音。由此可見,早在秦始皇之前,「正」字有「正」、「征」兩音,因此為避始皇正的「正」字而讀作「征」,實乃穿鑿附會之說。
陳垣在「卷八」臚列歷朝諱例,由秦漢至唐宋,下迄明清,所諱之字,一一列明,實在有助後學知曉。可惜本文篇幅所限,無法詳敘;反而想在此說明,避諱之舉,雖說歷代皆有,但有些朝代,皇帝為免麻煩,確曾下旨停止或減少避諱。例如唐高宗顯慶年間,曾下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更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由此可見,皇帝為了宣儒尊孔的大原則,雅不欲因避諱而貿然更改古籍,因此但凡舊典文字,不予更改。這也是古代避諱大環境下一種適可而止的做法。
為沈刻《元典章》校補
陳垣除了寫就這本「能應用之於校勘學」的《史諱舉例》之外,亦於隨後的一九三一年寫了一本直接關乎校勘學的書,叫作《元典章校補釋例》。此書校補了沈刻的《元典章》,(按:「沈刻」是指晚清沈家本在書內題跋的刻本),而《元典章》是一本「考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不可少之書。」(見書內「序」)為什麼陳垣要為沈刻《元典章》校補並給予釋例呢?
原來他向學生講授校勘學時,要舉例說明,總覺得如果廣引群書,則檢對不易;如果單引一書,則例子不多。當然,如果例子多,則表示書內錯誤多,而如果某書錯誤多,則表示該書未必是本好書。碰巧沈刻《元典章》是一本性質重要但錯誤極多的好書,十分適合做校勘學的反面教材。陳垣在校補沈刻《元典章》時,得出謬誤一萬二千多條,並將當中十分之一疏釋,編成《校補釋例》。由於此書只校補沈刻《元典章》,書成後因而定名《元典章校補釋例》。不過,陳垣鑒於此書實在可以當作校勘學的範本,於是改稱為《校勘學釋例》,而隨後學術界但凡引述此書時,皆棄舊從新,稱之為《校勘學釋例》。
此書共分六卷,依次是「行款誤例」、「通常字句誤例」、「元代用字誤例」、「元代用語誤例」、「元代名物誤例」、「校例」。從上可見,陳垣把諸般勘誤分門別類,然後按着門類逐一羅列。例如「卷二:通常字句誤例」下,細分為:「形近而誤例」、「聲近而誤例」、「因同字而脫字例」、「因重寫而衍字例」、「因誤字而衍字例」、「重文誤為二字例」、「一字誤為二字例」、「妄改例」、「妄添例」、「妄刪例」及「妄乙例」共十一類。
從上可見,陳垣在勘誤過程中,把看到的錯誤清晰分類,而這種極其科學的校勘法正正是此書的最大貢獻。誠如作者在書「序」言明,校勘補正的用意,是把一本值得後人閱讀的好書,盡去糟粕,使之更為完善,而絕非存心齮齕。其實這就是校勘的良善本意。
此外,但凡治理學問的人當必明白,校勘是一門沉悶乏味的工作,而唯一的樂趣,恐怕是在校勘歷程中找到錯誤而為之一一訂正,俾能惠及讀者。必須在此指出,別以為校勘學應用範圍狹窄而因此輕視;其實此門學問應用範圍極廣。小莫如文字工作者每天須做的校對,也應該運用得上。只要我們緊記諸般校勘法則而套用於日常的校對,當必暢順無礙。
如果大家不厭其悶,喜歡探索校勘學,除陳垣《校勘學釋例》,亦可翻閱校勘權威張舜徽的《廣校讎略》、《校讎學發微》、《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及王叔岷的《斠讎學》及《斠讎別錄》等書。
《華化考》以西域人為緯
身為史學大師,陳援庵亦精研民族史,而他對元朝西域華化的論述,早在二十年代已於學報發表。起初的四卷在一九二三年初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而後來的四卷在二七年刊於《燕京學報》。及至三五年,他將前後共八卷的論述合訂為單行本,取名《元西域人華化考》。
書內八卷除「卷一緒論」及「卷八結論」外,其餘六卷依次是「儒學篇」、「佛老篇」、「文學篇」、「美術篇」、「禮俗篇」、「女學篇」。由此可見,文化領域裏的思想宗教、文學美術、生活禮俗,無所不包。尤其特別的是以專篇論述西域婦女的華化情況。
陳垣在書內暢談西域人各方面的華化情況之前,先在「卷一緒論」內說明西域的界定範圍、元朝西域的文化狀況、華化有何意義,並且介紹元朝之前的華化先驅大食國人李彥昇、安息國人安世通及西域人蒲壽宬。至於書內所界定的西域範圍,是專指畏吾兒(即維吾爾)、突厥、波斯、大食、敘利亞等國。
陳寅恪為陳垣書作序
此書的特色之一,是以宗教思想、文學美術、生活禮俗為經,以歷朝及各地西域人為緯。換言之,他以個別西域人概述華化情況。書內所論及的西域人,合共一百六十八人。當中以文學人數佔最多,有五十一名,女學最少,只有六名。此外,陳垣在書末抄引元人的文稿,從而探知「元人眼中西域人之華化」。從元人的角度看華化,更見恰當。
《元西域人華化考》除題材有趣、內容豐富、鋪排有致,更有另一特色。不過,這一項特色居然與書內正文無關,而是與書序有關。何解?原來為此書作序者,並非別人,而是「史學二陳」的另一「陳」,即陳寅恪。此舉足見兩位史家情誼匪淺,盡展謙和切磋的風範,實在是學林佳話。
陳寅恪治學嚴謹,即便為人作序,亦絕不視之為酬酢而滿紙恭維,行文浮泛。他在這篇大約只有一千字的序文申明清代史學遠遜宋代。他首先推翻時人的錯誤判斷,以為滿人「入主中國,屢起文字之獄、株連慘酷,學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於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閒(按:即「間」,下同)之載記耳。其他歷代數千歲之史事,即有所忌諱,亦非甚為礙者,何以三百年間史學之不振如是?是必別有其故!未可以為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抑之所致也。」
陳寅恪進而指出,經學與史學儘管同屬考據之學,而治學者雖然號稱樸學之徒,但兩者性質差異極大:史學材料大都完整,詮釋上極有限制,經學的材料往往殘缺寡少,經學家因此可以自行詮釋。如此一來,經學根本難以衍化成有系統之論述。因此那些「樸學之徒」取易捨難,刻意發展經學而捨棄史學。陳寅恪慨言:「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以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按:即「捨」)史學而趨經學之一途。」史學結果淪為老儒官宦退休後「老病銷愁送日」的工具。
對於陳寅恪「清代史學遠遜宋代」的論說,陳垣門生牟潤孫曾有補充。他在一九八二年發表的「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一文內首先指出,清代史學考據的著作,雖然數量上的確少於宋代,但品質並不算差,甚至可比宋人。不過,學術界絕對沒有不撰寫史書或史論而只是專門考據史學的人可以稱為史學家。牟潤孫進而指出,清代史學式微,主因在於皇權介入,而歷朝皇帝干涉修史的惡例,始於康熙,至雍正最為激烈。
牟潤孫這篇文章,原刊於《明報月刊》「第二○二期」,後收錄於《注史齋叢稿》(增訂本「下篇」)(六七六至六八三頁)。有興趣探索這個課題的後學,可將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序文與牟潤孫此文一併研讀。
備課嚴謹 訓誨溫柔
至於陳垣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一書,其實是陳垣本人、門生來新夏及陳垣之孫陳智超合共三代的著作匯編。書內既有陳垣為講學而擬備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講稿」及「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教學日記及札記」,亦有來新夏在一九四三至四四年恭聽陳垣講學的筆記,以及陳智超兩篇短文,即「百世師表」及「千古師生情」(按:後者指陳垣與另一學生柴德賡的師生情誼)。
我們作為後學,閱讀這本小書倒有不少益處。其一,可從「名著評論講稿」和「日記及札記」管窺陳垣備課嚴謹不苟的態度。其二,可從來新夏的筆記推想學生當時領受教澤的情況。其三,可透過孫輩記敘陳垣師生情誼而深深感受到這位史學名家既是治學嚴正、論述精微的學者,亦是力扶後學、溫情訓誨的老師。
要全面介紹陳援庵其人其學,斷非一篇短文所能達致。只希望這篇膚淺孤陋、片面不全的劣文,可以喚起後進探究陳垣史學成就的丁點興趣。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
- 凡本網註明"来源:華發網繁體版的所有作品,版權均屬於華發網繁體版,轉載請必須註明來自華發網繁體版,https://china168.org。違反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 本網轉載並註明自其它來源的作品,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不承擔此類作品侵權行為的直接責任及連帶責任。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轉載時,必須保留本網註明的作品來源,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
- 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周內與本網聯系,否則視為放棄相關權利。
- 李家超:破壞力量仍然存在 絶不能掉以輕心
- 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 香港分會場氣氛熱烈
- 特區政府斥英國報告抹黑新選制
- 梵蒂岡任命香港主教!「反港獨」神父周守仁擔任,臺唯恐面臨斷交
- 深圳推《前海方案》44條 支持港高校建新研究機構
- 把握机遇/港借“双循环”打造法律服务平台
- 林鄭月娥:破壞國安不能接受 有信心警方妥當運用權力
- 融入“雙循環”的香港明天會更好
- 要求加拿大釋放被美國 迫害的中國公民孟晚舟
- 梁振英:激進化如毒癮禍害青年
- 1《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鄭宇碩收美國錢搞「佔中」鐵證陸續曝光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政治和法律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一切鼓吹國家分裂的主張和行為,衝擊「一國兩制」,背離「一國兩制」與基本法。鼓吹「港獨」的政客和團體,在香港沒有任何生存空間,[詳細]
- 2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

這是一本自述體的書籍。作者根據自己擔任占中組織者的助理期間,在日常工作中接觸到的大量真實資料,經過細心的整理而成。當占中組織者信誓旦旦地公開說謊誤導香港民衆,沒有外國勢力參與占中活動的時候,由作者披露出的事實卻是,外國勢力主導和支持了占中等[詳細]
- 3愛國愛港就要勇敢地亮出來——夏雲龍博士與香港民間團體交流會紀實

6月3日下午,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華發傳媒總裁夏雲龍博士一行3人,在香港觀塘巧明街迅達工業大廈8樓A座的保健海流協進會辦公室,參加香港民間團體負責人座談會。該座談會主題為“愛國愛港亮出來”,由保衛[詳細]
- 4田飛龍:港青國民意識現危機 須重啟國民教育

田飛龍“占中”的重要政治遺產就是香港青年世代走上政治舞臺,形成香港社運新生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既[詳細]
- 5美國「以港遏華」和「以華制華」的政治陰謀路人皆見

從中美貿易戰開始,我便估計香港難以置身事外,不能倖免,過去數月香港發生種種示威遊行,均有美國的手影存在,現今想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更是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務,並展示對亂港派的支持。 [詳細]
- 6從《何為證據》看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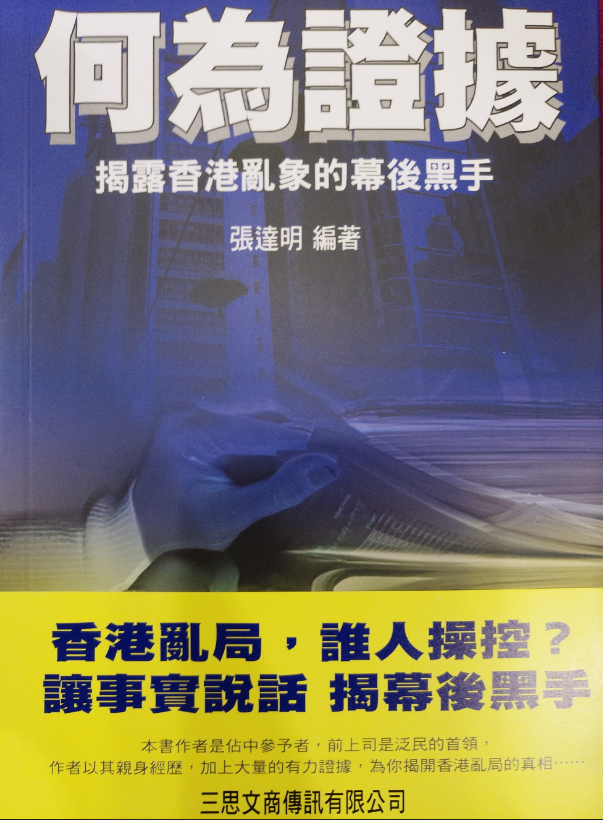
《何為證據》羅列了一系列極具震撼力的證據,「揭露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讓讀者有機會看清「佔中」背後的外國勢力身影。編著此書的張達明先生不顧視力受損,在過去七年鍥而不捨地蒐集和整理第一手資料,以鄭宇碩的言行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披露「佔中」背後[詳細]
- 7法庭對犯罪審判的輕判或拖延,都是對正義的否定

2016年3月31日下午2:30 - 4:30,由亞太法律協會主辦、香港公民協會合辦的【“佔領運動”以來的相關案件評析報告發佈會暨研討會】在香港中環中心專業聯合中心B報告廳舉行。報告會由香港公民協會林國華主席主持[詳細]
- 8“港獨”不除 國家安全堪憂

香港的 “港獨”分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不會輕易拋頭露面,他們躲在背后煽陰風、點鬼火,或是暗中提供資源等幫助,或是明火執仗為涉嫌違法犯罪分子狡辯;第二類是以學者身份、藉理論探討之名,向第三類 “港獨”分子灌輸 “港獨”思想,他們的歪理雖然[詳細]
- 9【香港書展2018】《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新書簽售賣爆現場

7月18日上午,香港作家張達明攜新作《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亮相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詳細]
- 10吳鵬飛:給港獨敲響一記警鐘,也給國家提個醒

港獨最近鬧得很凶,先是有人在英國註冊香港獨立黨,後來又有人在香港成立事實上以港獨、公投制憲為政綱的政黨,其發起人又是要參選立法會議員,又是應邀到美國大學演講,又是寫文章鼓吹。表面上好像很熱鬧,實際上是[詳細]
- 11嚴懲黃師黑暴 執政者快上訴

我們「保衛香港運動」代表全港市民,强烈不滿及堅決反對法官高浩文放生多次發表仇警言論的黃師譚玉芬,她企圖煽動羣眾攻擊傷害警員及其家屬,也令入世未深的學生和年青人觸犯暴動罪而前途盡毁。 社會大眾在2019年[詳細]
- 12嚴厲警告歐盟 停止詆毀香港

今日我們「保衛香港運動」來到歐盟駐港辦事處這裡,是要强烈譴責歐盟及七國集團抹黑香港國安法,誣衊23條生效後在香港生活、工作和經商變得更加困難。我們嚴厲警告歐盟及G7立即停止損害香港國際聲譽、立即停止干預屬[詳細]
- 和氣生財6/李家超:推廣禮貌服務 提升香港魅力
-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赴北京述職
- 吸引力足/寧德時代來港落戶 設國際總部及研發中心
- 免簽生效 到中國經商旅遊更方便
- 特區政府斥美打「法案牌」干預港事務
- 高鐵載客量超越疫前 短途增幅大
- 民進黨處心積慮搞「台獨教育」
- 市區「輕微僭建」 研申報後暫緩執法
- 情牽兩岸/創業台青深耕國漫IP 傳播中華文化
- 施政報告前瞻/設中醫藥專員 建數碼化中藥平台
- 兩岸京劇一脈傳 好戲連「台」見情深
- 投資信心提振 恒指連升六日共千點